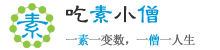阿天的舌头在黑糊糊的碗底舔了又舔,还是不肯挪开。阿地伸手夺过那碗,啪的一声摔碎,有一粒饭米不知打哪儿跳了出来,偷偷地躲在地上。阿天扑过去,用舌舔起来,再把它卷在舌心里,贪婪地用浓浓的口水滋润着。
阿地深凸、发亮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阿天的嘴,好久才把目光移开。望着慢吞吞爬向天空的月亮,阿地说,走吧!
阿天咽了下口水。
寒风剜咬着肌肤,阿天拽拽衣领,哧啦一声,衣领掉了一块。阿天莫名其妙地骂了一句,缩着脖颈,跟在阿地的后边。阿地猫着腰,只顾往前走着。
还很远吗?
是的。
这鬼天气,阿天哭丧着脸,走路也不暖和。
那就走快些。阿地语气硬硬的。
沉默,更增添了寒夜的阴森。路边光秃秃的树干,涂着冰冷的月色,经风一吹,响着痛苦的呻吟。
过了那片荒地,就是江边了。阿地细细的声音划破短暂的沉默。
可是,阿天的声音颤抖起来,要是让鬼子撞见了,怎么办?
阿地站下来,等到阿天靠近了,甩起脚猛踹过去,还凶:没有别的办法了,你懂不懂?阿天躺在地上,想了半天,还是爬了起来。阿天知道,也只能这样了。昨天,他们摘了一千多个衣扣,可还是没有换饱肚子。要是再摘不到更多的衣扣,那还不得活活饿死。想到这里,阿天真想说,阿地,不躲了吧!可阿天没有说。阿天知道,就是说了,阿地也不会同意。天天有那么多人被杀被活埋,想想都毛骨悚然。阿天只好硬着头皮,咬在阿地屁股后面。
有光束在不远的地方扫。
是拉尸的车队,阿地按倒阿天,别出声。
他们趴在荒地的凹沟里,抬着脸,心里默默地数着:一辆,两辆,三辆
数着数着,阿天有些兴奋了,小声说,好多呀。还说,能摘好几千衣扣呢。阿地没做声,只是拿眼睛在阿天脸上剜割着。阿天觉得阿地的样子怪怪的,就也闭了嘴。
月亮冷着脸,泻着凄清的银辉。
走了,你看他们都走了。阿天从凹沟里爬起来。
阿地还是没做声,只是猫着腰,往前走着。
江水就在眼前,凄清的银辉下,漂浮江面的尸体安详而寂然。他们跑到江边,拉过一具具尸体,摘下他们的衣扣后,再把他们推过去。妈的,你割着我了!阿天发现,面前的这具女尸,她的头发里插着一把短刀,也就是这把短刀,割破了他的手指,他在伤口上洒了些沙土,顺口吐口吐沫,继续摘着衣扣。阿地摘了会,情绪陡然跌落。看着面前的一具具尸体,阿地想,世界似乎太不真实了,像是梦里的情景,一个小时或者更短时间以前,这些尸体,可能都还是鲜活的生命,可是现在
阿地,阿天抱起一个婴儿,惊着声音,这不是红妞吗?
阿地扑过去,抱过婴儿,婴儿右手的中指和食指还放在小嘴里,瞪大着眼睛,像是被什么东西吓着了,一脸恐怖。
阿地吼:小鬼子,我操你祖宗。接着便是大声恸哭。
阿天也哭。
哭声在江水里翻卷着,传出去很远很远。
最后,他们在江边扒了个坑,将尸体放进去,盖了些石块在上头。望着隆起的石块,阿地说,走吧!
阿天没有挪步。
阿地催促,快走呀!
阿天走了,走着的阿天正思想着这些衣扣足可以换得一顿饱餐了,却听见嘭的一声响,回头一看,阿地撞死在那堆隆起的石块上。
阿地——
阿天声嘶力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