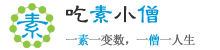我的办公室位于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麦格劳·希尔大厦。一个周五的晚上,我正在加班,中途离开大厦去抽了支烟,然后回头走进大楼,走过正在擦拭大理石地面的家伙,走进电梯,按下43层的按钮。
电梯上升途中,我感觉到一阵晃动,灯光暗了片刻。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电梯停住了,于是按响了紧急警铃。我气坏了,因为我的截稿时间快到了。当时我是《商业周刊》杂志的出版经理,必须让杂志按时出来。我期待有人回应,可是没有人。于是我再次按下按钮。我想大声喊叫,但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我不想大惊小怪,所以只是任凭铃声响个不停,然后等待着。
但还是没有人。当时是周末,只有很少人还在工作,而且大楼里一共有32部电梯。万一在周一早上之前都没有人发现我该怎么办?我试着摆脱这种想法,但随着警铃不断响起,无人应答的时间越长,我脑海中横尸电梯的画面就越是挥之不去。
我开始撬门,想看看能不能出去。但当我把电梯门扳开时,只看到了水泥墙面——电梯井道的墙面。这反而让我的受困和受挫感更强了。我沿着电梯的内壁向上攀爬,打算去敲开天花板上的活板门。我知道离开电梯会很危险,但我已经顾不得了。可是,活板门上了锁。
我躺在地板上,完全绝望。慢慢死去的想法将我吞噬。我只剩下几支香烟,也没有吃的和喝的。我试着睡觉。当我转身侧卧时,我注意到电梯的地毯上有零星的指甲、皮肤碎屑和头发。我觉得很奇怪,在乘电梯那么短暂的时间里,人们身上怎么会抖落下这么多东西。我暗自下定决心,如果我能最终逃出电梯,一定要请上一两天假,好好享受一下。
几个小时过去了。然后是更漫长的几个小时。我完全丧失了时间概念。突然,对讲机中传来一个声音:有人在里面吗?我跳起身来大声叫道:该死,赶紧把我从这里面弄出去。四十分钟后,一点预兆也没有,我感觉到一阵气流,同时电梯开始移动。电梯门打开了,我像软木塞一样蹦出电梯。我向电梯机械师询问时间。下午4点,他说,星期天。我在电梯里待了41个小时。
第二天早上,记者包围了我的公寓。我所说的只言片语都出现在报纸上。《商业周刊》的公关主管问我要不要住到酒店去,直到风暴平息。接着,不可避免地,律师们开始给我打电话,抛出一个又一个数字。有人声称能够拿到2500万美元作为惩罚性损害赔偿费,并建议我不要工作了。因此,我不再工作,开始了这种梦一样的生活。我失业了,但却开始考虑购买200万、300万美元的公寓。
我和其中一名律师签了约。2004年,也就是电梯故障发生5年之后,我们上了法庭。我不喜欢站在证人席上的感觉——内心非常恐惧。我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未来,全指望着巨额的赔付。最后,我们达成了庭外和解。我不能透露数额,但那是一笔像样的钱。我拿到了六位数。
一切鲜活的生命都害怕陷入困境。在那台电梯里,我真的感到恐惧。但是我犯了个错误:爬出来,以及延长了自己受困的时间。过去我的生活状态很好,直到我开始寻求巨额赔付,这毁了一切。我没有工作,也一直没有结婚。我走进电梯时过的是一种生活,走出来的时候,却步入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但是,毁掉我生活的并不是那部电梯,而是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