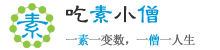要进站时,大姐站在风中冲我挥手,她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蓬乱。我转过身去快步走,不敢再回头看她。
爸妈走了,还有姐姐
爸妈出车祸去世那年,大姐17岁,正上高一,而我和我的双胞胎弟弟小杰刚读到小学五年级。
我还记得那天不断有人到我们家里来。他们说的什么、做的什么,我都忘了,我只记得我和小杰不停地哭。我们陷入到失去父母的巨大恐惧中。后来大姐紧紧地搂住我们,用嘶哑的声音说:别怕,爸爸妈妈走了,你们还有姐。
丧事办完之后,大姐退学去了爸妈原来工作的印刷厂。
本来她还不到上班年龄,但她一趟趟地去求厂长、副厂长。人家觉得我们姐弟三人可怜,才破例让她进厂。
刚上班那会儿,因为劳动强度太大,大姐累得晚上做梦都哎呦。她手上常常有被纸划破的口子。渐渐地,手指关节都有些变形。搬运东西太多时,她的腿都会变得一瘸一拐的。但即使如此,她也会一瘸一拐地走回家,用她粗糙而变形的手给我和小杰做饭。
周围人都心疼大姐。她本是我们那条街上最漂亮、文静的女孩,但家庭变故后,她变了。她剪掉了长发,穿上肥大的蓝布工作服,看上去像个假小子。她的性格也变得泼辣,为了跟婶婶要回少得可怜的抚恤金,她在叔叔家门前撒泼打滚;买菜时为了砍掉一毛钱,她很大声地跟小贩争论;晚上有人在我们家门前吹口哨,她操了棍子就冲出去。
你们踏踏实实上学,什么都别管
高中毕业时,我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而小杰落榜了。但大姐说,无论如何,也要送小杰去学点技术。可平日里,大姐抢着加班,每月精打细算,也没能省出一分钱,又一下子去哪儿拿这两笔学费?
那段时间,大姐心力交瘁,她顶着黑眼圈四处借钱,叔叔家、表姑家但一无所获。
离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一天傍晚吃饭时,我说:我不想上学了,我想工作。大姐白了我一眼:说什么傻话。你才18岁,不上学,能干啥呀?
你不是17岁就工作了吗。我低着头说。
大姐老半天没说话,后来才缓缓开口:就因为我那么早就上班了,才不想让你们跟我一样。你俩什么都别管,就踏踏实实准备上学吧。
饭快吃完了,大姐忽然说:有个事儿跟你们说一声,我要订婚了,跟顺子。
我和小杰都愣住了。大姐说的那个顺子,就住在街西头。他爹开了个剃头馆,他在那里给人理发。他人长得不好看,还是个瘸子。我接受不了大姐跟这么一个人订婚。
我知道大姐喜欢过街东头的小斌哥。小斌哥考上大学那年,还给大姐送过一套参考书,说她要是回学校读书,也能考上。大姐没有回学校,但我好几次看见她拿着其中一本参考书,愣神儿。
我和小杰还没有开学,大姐的订婚仪式就办了。
她彩礼没要任何东西,只要钱。订婚前一天,顺子爸把一个鼓鼓的信封交到大姐手里,说:这些足够你弟弟妹妹的学费了。只要你好好跟顺子过,以后他们每年的学费,我们都不会不管的。
大姐点点头,什么都没说。我的心像被刀子拉了道口子一样难受。
30岁的大姐,看上去已是苍老的妇人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大学所在的城市。我几乎不回老家了,因为总觉得大姐嫁人后,自己就没有家了。大姐再像以前那样给我寄生活费时,我会给她邮寄回去,顺便附上一些我的收入。
小杰要结婚时,我才再次回老家。我没有告诉大姐哪天回去。那天,下了火车,我径直打车回到了那条街。离家多年,这条街有了变化,旧房子都拆得差不多了,路边多了些商店和饭店。但老菜市场和那些旧平房还在。路过市场时,远远地,我听到了吵闹声,不禁驻足。
几丈外,城管在执法。有个摊贩在地上撒泼打滚,不让城管把她的东西拉走。那是个女人,穿着一件半旧的棉外套,头发随便扎在脑后,有几绺散落在被冷风吹得发紫的面颊上。她带着哭腔喊着什么,去跟城管争夺一杆秤,夺不回来,就坐在地上哭天抢地。
我望着她,心忽然被针扎了一下,痛起来。那个正在哭喊的女人,是大姐。半晌,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但后来选择了逃离。我绕了一条街回到家,望着还是老样子的破旧不堪的老房子,眼泪忽地涌出眼眶。
不一会儿,大姐回来了。她脸上的泪痕刚刚被风吹干,衣服上还沾着很多土。她看到我,先是嘴唇哆嗦了一下,然后才叫出我的名字,小颜。我忍着泪点头。才刚刚30岁的大姐,看上去已是一个有些苍老的妇人。
大姐走上来攥住我的手。她的手掌很粗糙,手背上有冻疮。她十分欣喜地说:你来家也不说一声,我去接你啊。这房子好久不住了,冷,你跟我去我现在住的地儿。
大姐拉着我,来到她现在的家,一套六十几平方米的旧楼房,是当年瘸哥母亲的单位分的房子。大姐拉我坐下,你一定饿了,想吃什么,大姐给你做
家里菜不多了,你要吃什么,我出去买。她絮絮叨叨地说着,那样子让我想起母亲活着的时候。
我问大姐近况如何。她告诉我,印刷厂去年倒闭了,她现在在路边摆摊卖东西,生意还行。瘸哥那个剃头馆,受到美容美发行业的崛起,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不过糊口没有问题。大姐的话轻描淡写,但我知道这里面包含了多少无奈和辛苦。
小杰结婚后第二天我就离开了老家。大姐送我到车站。要进站时,大姐站在风中冲我挥手,她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蓬乱。我转过身去快步走,不敢再回头看她。
她总想着我们,从没想过自己要什么
几年后的一个冬天,男朋友向我求婚,我跟他说:跟我回家一趟吧,结婚的话,得我姐同意。
男友有些诧异。我其实也诧异自己会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话。可是在面临人生重大的抉择时,我的脑海中刹那间就想到了我姐。
我领着男友走进我当年生活的大街,这条街变化更大了。一些房子已被拆掉,没有被拆的,也标上了拆迁的标志。在一片断壁残垣中,我们一步步走向我的家。
推开院门,一股面香扑鼻而来,大姐正在厨房忙着做面。我们走到厨房门口,大姐正巧出来。她看看我,又看看我身边的男友,无比欣喜道:回来了,回来了!嗯,一会儿准备吃面。知道你们要回来了,我早回家煮了面条,出门饺子回家面,咱们吃面。
大姐的汤面做得真香,暖心暖肺的,男友吃了两大碗。大姐很开心,悄悄地跟我说,这个男人不错,看上去斯文,人又实在,我跟他结婚,她就放心了。
大姐还跟我说,小杰当初结婚,女方嫌弃房子太破时,大姐就将自己的楼房换给了小杰。而现在,老房子要拆迁了,小杰又想把房子换回来。我想为大姐打抱不平,大姐笑笑说:我原本也没打算要这房子,小杰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要是你不打算跟他分房产,这房子就归他了。我当然不打算要房产,可我觉得大姐这些年太委屈了。大姐拍拍我的胳膊,你和小杰过得好,大姐比什么都开心。
我走的时候,大姐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这些年我寄给她的钱。我说什么也不要,大姐把信封硬塞进我怀里,姐没法给你更多,这些,你买点结婚用的东西。以后有了难事儿,回来找姐。
姐,你有什么心愿没有?临走,我问大姐。如果大姐说想旅游,我马上就请假带她去,如果她想要什么东西,我立刻就给她买。这些年大姐太苦了,她总是想着我们,从来没想过自己需要什么。
可是大姐只是拉着我的手说:大姐就希望你经常回来。我含着泪点了点头。
大姐依然是我的保护神
30岁这年,我遇到了一些坎坷,工作遇到了麻烦,婚姻也遇到危机。我心灰意冷,觉得生活没有意思,甚至几度产生轻生的念头。
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我走在空旷的街头,不知道该去哪里。不知道走了多久,我忽然发现我走的是去火车站的路。于是,顺着内心的选择,我去车站买了张回老家的票。
下了车,我直奔大姐开的面馆。在面馆门口,我看到大姐,她正从一辆车上往下搬白菜。大姐看到我,又惊又喜,放下白菜,在围裙上擦擦手,跑过来拉着我的手。
我一下子泪流满面。
怎么了,小颜?大姐吓坏了,一个劲儿问我。
没事儿,姐,我就是想你了,想吃你做的热汤面。我说。
大姐立刻把我拉到店里,去给我煮面。那碗面热乎乎的,卧了荷包蛋,放了香油,还有一小把绿油油的菜。
这味道,真熟悉,这温暖,不但让我的胃熨帖,让我整个人都不再寒冷。
我吃面的时候,大姐一直焦虑地看着我。等我吃完了,才问:小颜,遇到难事儿了吧?跟姐说,姐给你做主。刹那间,我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为了不让小杰受同伴欺负,拿着柳条杆子去送我们上学的大姐。
我摇摇头。我不用大姐跟我一起去解决,吃了大姐的热汤面,我又有力气了,我能解决自己的难事儿。大姐对我说:小颜,要是在外面过得不开心,就回家来,大姐现在有这家面馆,能养活你。我含泪点头。
那时,我才知道,大姐对于我多么重要。即便她成为一个历尽沧桑的平庸妇人,她依然是我的保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