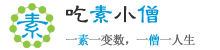一个高昂和挺拔的背影,一个被抚摸着长得这么大的背影,终于消失在匆匆奔走的人群中间,消失在候机大厅的尽头。真可惜自己的眼睛无法跟着他拐弯,要不然的话,就能够瞧着他登上飞机了;更遗憾的是自己这双眼睛,无法看见地球的那一边,要不然的话,就能够瞧着他在芝加哥走下飞机了。
当我正忧郁地陷入沉思时,肖风轻轻拉着我的手腕,我们俩的眼睛默默对视着,我怕她会哭出来,她却在凄婉的神情中,勉强地露出了笑容,像是自言自语地摇着头:为什么不再回头瞧我们一眼?
不算太大的候机厅,跨过去几十步路,就迈到了那一端,其实他已经有多少次回过头来。除非不远行,永远厮守在我们身边,否则总会有今日的离别,我们度过了多么闭塞和单调的青年时代,当儿子在吮吸着乳汁时,我们甚至连做梦都不敢想象,这逗人喜爱的小不点,能有远渡重洋去负笈留学的机会。
肖风说过多少回,我们早已失掉这样走向世界的机会,应该让儿子去外面闯荡一番,认识整个的人类,是如何打发自己日子的。大概是因为志向高的缘故,才出乎我的意料,止住了应该会流出的眼泪。
我们身旁有个也在送行的母亲,瞧着她儿子匆匆离去的背影,呜呜地哭了起来。我的心变得沉甸甸的,猜测着自己的儿子,此时已经坐在飞机上了吗?我突然回想起几十年前,自己比儿子现时还要年轻得多,最心疼我的母亲,希望我赶快离开令人忧伤的家乡,去上海的中学念书。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当我跟她告别上路时,她眼睛里也闪烁着像肖风这样痛楚的光芒,强打着精神嘱咐我:用功念书,别想念家里。我当时丝毫也没有觉察,她这颗疼爱我的心,已经沉甸甸地坠落下去,只有在今天我才懂得了,因为我这颗沉甸甸的心,刚在往下坠落啊!可是我已经无法向她倾诉了,只有默默地祝愿她,在泉壤底下静静地安息。
肖风怎么会变得如此坚强,竟还劝这位哭泣的母亲说:儿子去留学,多好的事。干吗要哭呢?
我觉得自己的眼眶里,正在涌着泪水,绝对不敢开口说话,怕这轻轻的震颤,泪水会掉下来,我默默地拉着肖风,悄悄地走开了。
回家的路上,望着一棵棵大树,在车窗外慌张地往后退去,像是很忙乱地跟我们挥手告别。我们轻轻地说话,回想儿子刚学会走路的那一阵,左手紧紧地拉住我,右手紧紧地拉住肖风,在绿茵茵的草地上迈步,也望着高耸的大树,望着天空里漂浮的白云。那一双乌黑的眼睛,闪烁着神往而又奇异的光芒,还老在咯咯地笑,我们一起瞧着他又大又亮的眼睛,想问他为什么笑,他当然还不会回答这样深奥的问题。
一个混混沌沌的儿童,怎么在瞬间就变成聪明而潇洒的大学生了?怪不得我的头发全都花白了。儿子有一回去天津讲课,询问我柏拉图和西塞罗的掌故,虽然都读过一点儿,却还是回答得不好,而且他的许多兴趣和爱好,也已经跟我们迥然不同了,譬如说他就否定了我们10多年前教他如何欣赏音乐的见解,认为这不是为了陶醉在迷人的旋律中,而是要宣泄人世间的烦恼和痛苦。肖风曾背着儿子悄悄地跟我说:大人这么爱他,他有什么痛苦?
每一代人总会有自己的痛苦。我迷茫地摇着头,顿时觉得儿子已经长大,已经走出了父母悉心给他营造的小天地。
在深夜里,3个人海阔天空地闲谈,是全家最欢乐的时辰。肖风提起了儿子的婚姻大事,这已经在她心里翻滚了许久。
想不到平时总乐呵呵的儿子,竟带着点儿伤感,带着点儿嘲讽的口气说:你们两位教授的工资加起来,都不及一个卖菜的小贩挣得多,能有漂亮的女孩儿,看得上生在这种家庭里的儿子?
肖风忿忿地说,人总得看本身的价值!
妈,收起你高雅的理想主义吧,它已经过时了。儿子轻轻拍着肖风的肩膀,阻止她再往下说,装得很深沉的样子笑了。
好胜的肖风,却不愿跟儿子辩论,隔了一阵才悄悄地跟我说:克林顿够了不起吧,可是在他母亲的眼里,永远是个小孩儿。
就是在那天晚上,儿子说要去考托福和GRE。很快考完了,考得很好,得到了芝加哥一所大学的奖学金。这时候我才清醒地意识到,儿子快要离开我们了。不是吗?他正坐在那一架远航的飞机上。
回家的路上,我们回忆着儿子小时候的事,刚开了个头,就到达了家中。推开门,觉得阴凄凄、冷飕飕的,尽管外面正是晴朗和灼热的盛夏天气,往日的欢乐都到哪儿去了?哦,在那一架刚离开地面的飞机上。我顿时又想起母亲送自己远行前的话:大丈夫志在四方!是啊,总得这样一代代地活下去,总得让年长的一代,去咀嚼人世间这苦涩的滋味。
肖风走进儿子的屋里,轻轻抚摸着他写字的桌子,抚摸着他今天早晨还睡过的被褥,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从今以后她会天天关心着芝加哥这陌生的城市,思念着儿子正在那儿干什么?她会永远悬着一颗心,祝福着那像谜一样遥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