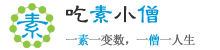10年前,当《东方时空》的白岩松还是年轻的小白时,年轻的小白曾说。渴望变老。那时,我觉得小白真是太年轻了,年轻得有些奢侈。
10年后,年轻的小白依然年轻,当年就不很年轻的我亩然年轻不再。但就有那么一天,当我看到一个巨幅招商广告:80岁,我们看海去时,我忽然有些动情,有些难以自制。其时,就觉得变老也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情。
在一望无际的大海边,在由一道细沙为蔚蓝色的海洋镶嵌的银边后,有一片绿缎子般的草坪,有几把白色的摇椅,摇椅上坐着我和同我一样年老的朋友。柔软的海风,带着几丝淡淡的腥味,轻拂着我的面颊。我的老朋友缓缓地移过来,帮我理了理那几丝随风舞动的银发,又帮我往上披了披我那有些滑落了的猩红色的披肩。我为老朋友冲了一杯随热浪翻飞舞动并溢出几缕淡淡清香的绿茶,又为自己冲了一杯香味低调而飞扬的雀巢咖啡。沐浴着和暖的阳光,临海凭风,我们颤颤巍巍地饮着,讲述着一些与海有关或无关的往事。讲讲他为我作的那首诗《我是海盗》,不知那时他是否还能记起?讲讲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不知道那时他是否还会那么动情?讲讲小时候河沟里摸鱼的故事?讲讲年轻时水库里游泳的趣事,讲讲成年后初见大海时那故作的深沉和过分煽情的激动?也许什么都不讲,就那样默默地看海,看海的深沉,看海的博大,看海风亲吻海浪;就那样默默地听涛声,听海的独语,听风与海的对话。
哪怕你一个字也不说,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要说什么。
豁牙漏风,海风硬。
有大海一样多的往事可以咀嚼,有大把的光阴可以供回忆,那应该也是别一种浪漫。
还记得在我最初成为老朋友的妻子时,我还十分年轻,年轻得有些稚嫩。就那样手牵着手走过十年后,老朋友曾剪下了我的一缕长发,用五彩线小心翼翼地包裹着珍藏起来,那时那一缕长发黑得闪亮。又是一个十年即将来临时,我又将头发慢慢留长,我知道这还会是一缕依然闪亮的黑发,但我知道再一个十年,我不会再送给他闪亮的黑发作礼物了,因为那时即使还有一些黑发,也不会那么长了。当我这么说时,我和我的老朋友都不约而同地叹了一口气,并为那一声叹息无可奈何地笑了。
80岁,我们看海去。我与我的老朋友相约。也许这一约定有些贪婪,也许这一约定有些奢侈,但正是这一约定,让那一声叹息远去了,让变老有了许多暖色。
我忽然理解了年轻的小白的渴望变老,虽然那是另一种变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