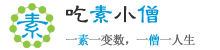穿过前面的隧道,再转上几公里盘山公路,就是市郊那平坦的柏油大道了。沿途的下客,那本来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上现在只剩下四个乘客一个司机了。淡黄的一抹夕阳与昏暗的山影交替着闪进车窗来,偌大的车厢显得有点凄凉。
看模样,那些乘客是利用假日去游山玩水回来的工薪族。崎岖山道上的颠簸,身子板再硬朗的人也被弄得七荤八素,人人垂目低眉,犹如佛祖打坐。
离城不远了,熟悉的景物催活了大家的情绪,一个个从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如释重负的伸起了懒腰。虽互不相识,却攀谈了起来——为了便于指认,我们不妨称之为甲乙丙丁。
甲先开了口:唉,这山路就是糟,再走上三公里,不用人家教我就自动会跳迪斯科了!
乙接过话茬:山路倒还可以凑合,就是这山里人啊,真是
本来嘛!深深吸了一口烟,丙吐掉浓痰,山里人没教养,愚昧粗野,治安极差!
丁一声不吭。他靠在车窗边上,正瞧着不远处那隧道口两个晃动着的身影。
夕阳的余辉隐进了群山丛中。一座庞然的山峰逼人而来,随即又闪晃到身后去了。
甲继续兴致勃勃的谈着:我看山区这旅游景点好多问题该有人来管管的了。
乙嗑着瓜子:可不是,听说前两天,有个旅游客被抢走钱包,还挨了一刀。
丙义愤填膺地:这种事听多了,可老子就是没福气赶上,不然话没说完,因为他又必须吐痰。
丁依然没说话。
汽车在隧道口突然停了下来,随即两个凶神恶刹似的大汉跳上了车。几乎还没来得及看清他们面容时,两把山民们砍柴用的小斧头就出现在乘客与司机面前,贼亮贼亮的。
听着,爷们要钱不要命!一个络腮胡子低吼着,沙哑的声音听了吓人。
甲离他最近,反应也最快。人家的话音刚落,他就哆嗦着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来,斜睨着身边那长满了毛的臂膀和那足以劈开山猪脑袋的斧子,再不见了刚才的口舌伶俐。
乙手中的瓜子全撒了。他很不利索的扒下一个戒指,对着人家不住的点头哈腰:呵呵,这个我那口子刚给我买的哦哦,是小了点
兄弟我就喜欢江湖朋友。先递上半包大中华,丙再奉上一叠各种票面都有的纸币,不成敬意,哥们尽管拿去喝壶茶!声音听起来有点飘,到底是想镇定自己或者又要吐痰,没人知道。
那胳膊,那斧子,现在指向了丁。只见丁慢慢地站了起来。慢慢的把手伸进西装衣襟里,第一次开了口——也是慢慢的:我是便衣刑警,不要逼我拔枪!
声音不大,可字字犹如炸雷。如同刚才上车时的速度,两个大汉转瞬跳下车,逃进了茫茫夜色中。
车上一片死寂,好久,好久。
终于,人们像刚从地狱还阳似的恢复了知觉,不约而同地呼出了一口长气,又不约而同地向丁靠拢了过来。
甲仍先发言,语气很诚恳的:老兄,真亏了你,不然说着,他又打了个寒噤。
乙边套着失而复得的戒指边赞道:神勇啊神勇,公安果然不同凡响,还没出手就把车匪吓跑!
丙拍了拍不很壮实的胸脯,豪言壮语伴着浓痰飞出口中:要是早知道车上有公安,我一个扫堂腿过去,就可以咽了一下口水,他看着丁的手,又补充了一句:真的,我不骗人。
丁把手从衣襟里慢慢抽了出来,手里握住一样东西,不是枪,是一个断了腿的太阳镜。借着朦胧的暮色,可以看见他的手抖得很厉害。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是假的
车开了,小心翼翼地驶进了隧道。大失所望的人们回到各自座位上,车厢又恢复了静寂。索然寡味伴随着睡意袭了过来,有人开始打起了哈欠。
汽车终于转上了柏油大道。司机踩开了油门,耳边只听得车轮与路面摩擦时那欢快的沙沙声。
天,全黑了。
突然,甲猛地睁开了眼睛,狠拍了一下大腿,黑暗中叫过乙丙咬了一阵耳朵,又摸到司机身旁嘀咕了几句。隐约听到他们的片言只语:假公安假枪哼,狗日的!
发动机突的吼叫了起来,汽车发疯似的冲向前面大桥边的治安值勤点。
前面,万家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