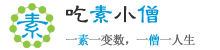如果有一天外婆再也不像孩子,不需要我们为她操心,为她欢笑,生活会多出一大片空白。
白天,家里只剩下母亲和外婆。空荡荡的房子里,两个人总是如影随形。
母亲走到哪里外婆就跟到哪里。母亲在厨房里烧菜,她就帮着做下手;母亲在客厅里读报看电视,她就陪在一旁织毛衣。外婆是母亲的尾巴,她害怕一个人,怕闲下来的孤独不适感。但口头上外婆拒绝承认这点,当母亲劝她多休息时,她一本正经地说:我总不能白吃小辈啊!
听第一遍觉得好笑,后来就觉得心酸。
外婆的子女儿孙们忙于事业,平日都不在家,最后留在身边的是头发也开始花白的老女儿。每次我回家,看着两位老人欣喜的样子,有说不出的自责。
我和外婆最亲密的接触只在晚上。白天,她和母亲的活动场所在一楼,晚上我们回家后母亲才有机会上楼。每当这时,外婆赶紧起身要跟着母亲一起上楼。她是小脚,上楼梯容易跌跤,我小心抱着她上楼。
可如果有客人在家,老外婆一定不让我抱。她仿佛少女一样羞涩,客人看着呢,你慢慢扶我就行。即便在美国生活了10年,外婆骨子里还有岁月抹不去的上海滩名媛的矜持。也因这份矜持,她一度无法接受自己衰老、日渐没用的现实。
一个学心理学的朋友说,对老人好,不是买礼物或者劝她多休息,是让她觉得自己有用,最好能保持以前的生活习惯,这样也能远离老年痴呆。
因这番话,我和母亲对老外婆劝得少了。八十高龄的老外婆像个孩子,什么都由着她,得哄着。老外婆喜欢检查抽水马桶,经过卫生间就会去抽一下,再一下,然后回头问母亲:水怎么老是抽不完,总会剩下些呢?水哗啦啦流走,母亲心痛水费也烦那时时响起的水声。可谁会真去阻拦老外婆的好奇心?
再譬如,外婆总要和我们一起出门购物。大舅怕她路上出意外,总会笑嘻嘻费尽口舌劝说她留下。可老外婆多会扮可怜,她知道怎样的表情最能让我们心软同意。逛街时的外婆最天真可爱,我们偶尔瞒着大舅带她逛商场,那是她最快活的时间,像夏日里吵吵闹闹后终于吃到冰激凌的孩子。她记性衰退,看什么都充满初见的新奇。我每每指着入口处那架正在工作的录影机的大荧幕,逗她:你看,我们全家都在里面呢,被拍成电影咯。外婆撇一撇嘴,回答也从来不变:哪里是拍电影,明明是大镜子,你当我不知道吗?
多数时候,老外婆坐在家中做她最有成就的事。家里大人小孩的绒线衫甚至沙发套、床罩,都是外婆一手编结的。她闲着没事,生产量惊人,多出来、穿不了的那些我们就当礼物送人。亲戚朋友听说是老外婆编结的,收下后都当宝贝放着供着,谁真会舍得用呢?没有人告诉老外婆真相,她觉得自己有用,干劲比年轻人还足,我们后来只得悄悄拆散她的成果,再绕成线团当做新买回来地放到她手里。
老外婆的针与线就像命运三女神的纺车,如果哪一天真的停下来,那一定是令人伤心的事发生。
外婆的记性很差,却始终没有忘记在国内的小舅。10年前,大舅将30余年未见面的外婆从大陆接到美国定居。那时母亲护送外婆一起到了美国。我和弟弟后来也举家到了美国。小舅成了留在祖国的孤家寡人,他曾办理探亲手续却没被批准。
让小舅来美国一家团聚,是老外婆最强烈的心愿。我们努力许多年后找到的唯一法子就是让外婆加入美国籍,再由外婆申请小舅来美定居。入籍必须考试。大舅给她布置了三道作业题:一,会签自己的姓名;二,记住美国的国父是谁;三,记住来美日期。第一题看似容易,外婆也苦练三周才让签下的姓名不歪歪斜斜。第二题倒不难,外婆念过私塾,小时候就知道华盛顿其人。第三题好比学唱英文歌曲,外婆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哼曲子般地用洋腔调背出了她的来美日期。还有最大的一难,是必须听得懂移民局官员用英文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刚学会英语不久的曾外孙女同外婆一问一答,忙得不亦乐乎。
考试那天,外婆提心吊胆进了移民局。高鼻子蓝眼睛的官员问外婆:你叫什么名字?或许是洋人的打扮太吸引人,也许是他的口音同曾外孙女相差太远,外婆呆了一会,脱口而出:华盛顿。
考试宣告失败。外婆皱巴着脸一路无话。大舅在外婆耳边轻轻地说:别急,还可以考第二次,下次再来。她一声不吭,像是没有听见。
晚上外婆拨通了小舅的电话:儿子,你自己想法子出来话没说完已老泪纵横。
天真可爱、语出惊人笑料不断的外婆,此时不过是个见不到孩子、伤心多年的老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