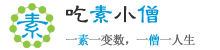世上的路千万条,但是,有些路是绕不过去的,是不能不走的。
小时候,爷爷经常带我去走亲戚。走亲戚,意味着能够吃上几顿比家里好得多的饭菜。这是爷爷对我的曲线疼法,使我得到许多实惠的慈爱。
爷爷经常去盘富村的那一家亲戚。不过,我并不爱去,因为必须经过一条七弯八折的厝弄,弄子两旁住的是猎户,养着好多凶猛的猎犬,那些猎犬帮助主人猎获过很多野兽,也给主人惹来不少麻烦,咬伤过好多陌生人,我害怕那些猎犬。
毕竟爷爷老了,爬山越岭,母亲不放心,叫我陪爷爷去,我岂敢说不?
在我踌躇之际,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螺号声。这是狩猎的号子。爷爷举起拐杖指着后山说:猎犬都在那呢,不要害怕了。
我顺着爷爷指的方向望去,隐约可见几个猎人正在管茅和芒箕丛生的山上,仿佛泅在水里围追着什么,猎犬异常兴奋的狂吠,此起彼伏,一浪又一浪地滚到我们的耳边来。
真的不用害怕了。
我又蹦又跳地走在前面。爷爷拄着拐杖,不紧不慢地走着,离我越来越远。我很快就到了那弄口,也许是条件反射,我停了下来,回过头,看看爷爷走到哪里了。看着爷爷慢吞吞的样子,我没有耐性等,便蹑起脚,试图像猫一样无声无息地通过那条恐怖的弄子。我才走进弄口几步,天哪,一声沉闷的恶吠,像平地惊雷,直轰我的耳根!我惊叫起来,仓皇四顾,不见一个人影。我家曾经养过母狗。我知道,这是一条正在哺乳的母狗,恶吠是它护仔的威严警告,哺乳期的母狗是最敏感的,也是最凶猛的,遇上这种狗是不能跑的,你越跑,它就追得越凶。而逃生的本能驱使我拔腿跑了。又惊又恐的我,跌跌撞撞地跑了几步,一条瘦瘦的黑狗摇摆着两排略显苍白的乳房,狂风似的呼啸过来。我双手抱头,双目紧闭。它先在我的右臀猛咬了一口。幸好那时正值隆冬,我穿了两条打了补丁的裤子,臀部的补丁又密又厚,狗的利牙没能深入我的细皮嫩肉,很不甘愿,又倏地爬上我的背,企图把我按倒,然后再慢慢地咬,要咬哪里就咬哪里,肥瘦任它挑。我又哭又喊,身体左摇右甩,可怎么也挣脱不掉抓住我肩膀的狗!幸亏爷爷闻声赶到,猛击一杖。我只听到咯的一声钝响,狗便翻了下来。
爷爷得意地说:打中的正是狗的最致命的部位——鼻梁。那狗趔趄着爬起来,垂头丧气地走进一个楼梯脚下的旮旯里。
爷爷搂住我,让我的脸贴着他的胸口,又是呼儿又是唤命,连连说:不用害怕,没被咬伤就好。
爷爷牵着我继续走,他自言自语:想不到这里还躲着一条产仔的母狗。
我又不伤害小狗,它凭什么那么咬我?我问。
凭什么?凭它对小狗的疼爱呀。
所有的母狗都这样吗?
是的。
我以后再也不走这条路了!
孩子,人一生在路上,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意外的事情,为了一个目标,有些路你不能不走,没有别的选择啊。
我一知半解地点了点头。爷爷笑了。我很少见到爷爷这样的微笑。
后来,我独自多次从那条弄子穿过。弄子两旁住的还是那些猎户,还有好多猎犬。只是我不再穿有补丁的衣裤,而是像爷爷那样,拿了一根拐杖,雄赳赳、气昂昂而不是畏首畏脑、缩手缩脚地走着;那些猎犬好像识相了,一般只在远远的地方狺狺狂吠,只有一二条追逐过来,甚至狂吠着尾随到弄子的尽头,当然,没有一条胆敢逼近。
该走的路,就大胆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