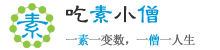在他们班的校友录里,我得知了他的现状,在南京一家化工厂上班。相册里,他笑容满面,身边依着一个温柔的、已有孕的妻。这是整场青春记忆过后,我唯一的慰藉。
一
15岁时的我,有个习惯,一旦心里塞满委屈,便跑到离街道不远的那个废弃厂房,坐在锈迹斑斑的大机器上,将每个指头包括脚趾的指甲剪个遍。厂房有小半个操场那么大,里面堆满陈旧的机器,氧化后它们只能被称做废铁。废铁也有人要的,一斤八毛钱,在那个一碗刀削面一块五的年代,觊觎的男孩子有不少。
看守这里的伯伯逮住过几个,送到派出所,一说叫老师,人就瘫软。学生嘛,总归怕老师。
我除了怕老师,还怕那个家。50平方米的旧单元房,5个人住,二伯二伯母,堂哥堂妹,还有我。每天清晨起床,二伯母的声音永远那么尖细: 江海,你昨天帮我买盐找的零钱呢?什么?没有?那我告诉你,今天的早餐费也没有,你以为咱们家是金库,我和你爸养这么多人容易吗?
江溪,你头发还没梳完?你是相亲还是上学呀?什么?梳你堂姐的头发?你怎么好的不学,光学一些不三不四的。
我永远是默默无声的那一个,努力将自己缩小,缩小,可这50平方米的房子,因为我的存在,显得更加狭窄。不是没有自己的家,父母厂子破产后,去深圳打工,我被寄养在二伯家。妈妈信里叮嘱我,人要知道里外。
外人就不该孩子们分糖你也抢,就不该吃完饭抬起屁股就走,更不该恰好你在家时家里丢东西。
算你倒霉!我坐在厂房的机器上,给剪好的指甲涂一层淡蓝色指甲油。那年,小地方的人只知道红色指甲油,妈妈从深圳寄过来一瓶蓝的,让我送给二伯母。
我没来得及送,抽屉里的钱就少了,二伯母将江海和江溪骂个半死,对我却是一个字也没有说。后来,抽屉换了锁,比以前更大更重的锁,硕大的钥匙挂在二伯母的裤腰带上。邻居见了常调侃,二伯母少不了一番诉苦:你不知道,家里人多啊,人多嘴多,眼多手多哟
那次丢钱后,我就成了这个家臆想中的贼。晚饭后,大家都去串门,我忙着看借来的金庸小说。二伯母遛一圈回来,坐在沙发上不停往我这边瞟。我明白了,提着书包跑到巷口,坐在报刊亭外的小板凳上,继续有滋有味地看。看到黄蓉偷人家的馒头喂狗,然后戏弄饭馆掌柜,我不禁向往起来,偷窃的乐趣果真这么妙吗?
我从书里抬起头,报刊亭的大妈正在给小孙子擦鼻涕,小孙子哭天喊地地反抗着,旁边一个织毛衣的妇女看热闹。我又想起二伯母一家防我似贼,心里有个声音跳出来:我就当个贼给你们看看!鬼使神差,我顺手将一本杂志放在书包里,拎起包扭头就走,骨骼肌肉都要被心脏撞个血肉模糊,没走几步一头碰到电线杆上。大槐树下乘凉的妇女们,齐刷刷冲我大笑,这孩子,看书看得入迷了。
这世上有烟瘾、毒瘾、酒瘾,就有偷瘾。胆子大了,我的手逐渐伸得更远更长:学校门口小摊上的造型橡皮、帽子店带檐的少女帽、饰品店里的五彩耳坠。偷来的东西大部分都扔掉或者送人了,乐在其中的不过是偷的过程。
二
班里组织大家到邻市旅游,我回家给二伯母提了提,二伯母尖细的嗓门立马跳出来: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物价飞涨,你爸妈给的那点钱吃饭都不够,上个月给你买的那身衣服还是二伯母掏的钱呢!我很乖巧地点点头,心里却明白,爸妈给的钱养活两个我都够了。委屈的时候,又想到那个废弃厂房,我的心生了锈,和那儿的废铁废块有什么不同!
脑子里灵光一现,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冬天的黄昏,来得特别早。我借口不舒服,向老师请了假,提前离开了学校。驾轻就熟地翻过厂房一人高的围墙。厂房的门用铁链锁着,但用力推,可以推出半人宽的缝,费一点劲就过去了。铁块很多,我随便捡了几块装进书包,又轻车熟路地钻出去。
路过厂房旁的小屋,里面的灯亮着,我忍不住侧耳听了听,没有任何动静。好奇心驱使,我踩在堆在窗户下的煤堆上,朝里面看,吃了一惊:那个伯伯靠着床坐在地上,眼睛紧闭,旁边的火炉上,热水壶咝咝作响,水壶下一缕缕灰烟不断往外冒。
煤气中毒!我下意识就要大喊,但张开嘴却什么也喊不出。我是谁,我来干什么,我为什么会发现这一切,这些问题砖一般砸在我脑袋上。我想象着那个场景:我被扭送到学校,老师和学生围在我周围唾骂,你是贼,你是贼;二伯母也来了,她冷笑着告诉大家:我说的没错吧?她就是个贼。然后,父母也来了,妈妈哭得伤心欲绝,爸爸冷冰冰地看着我。
寒风吹醒了我,眼前飘起了鹅毛大雪。我不敢再多想,背着书包朝家里狂奔。
那晚,我发烧了,昏昏沉沉的,书包被我死死地压在枕头下。还好,大家都顾不上我,二伯父给我喂了些药,一大早就上班去了。我挣扎起身,将书包里的铁块扔到巷口的大垃圾桶里。做完这一切,我才发现,世界已经被白色覆盖,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从此深深落在我的记忆里,掩埋住一切。
直到很长时间后,我才知道,那个伯伯煤气中毒,第二天被人发现时,已经救不活了。从此以后,我的噩梦永远离不开那个厂房。这个噩梦榨干了我,蹂躏着我,将我压成一个恐慌怯弱的少女。
厂房旁的小屋搬进新看守员。有一次,我在学校门口看到他和一个男孩子在一起,听他说:我在床下捡到一个水杯,可能是你爸以前留下的,你放学来取一下。
我费了一番周折才打听到,男孩叫杜小鸣。我用很蹩脚的途径认识了他。我竭尽所能地对他好,女生流行编手链,我一口气编了三条送给他;他学习很紧张,常常在教室学习忘了吃饭,我主动把买来的饭菜送到他教室。
我企图用这种方式减轻心里上的折磨,却不知,年少的我在他心里注入的暖流已然变味。
三
初中毕业时,父母在深圳稳定下来,我被接到深圳读高中,一晃就是10年。15岁到25岁,我华丽蜕变,再也不是那个被任何人都能捏圆捏扁的少女了。
二伯父一家来深圳旅游,我们一家为他们接风洗尘,在人声鼎沸的海鲜店,堂妹说:堂姐你记得咱家丢钱那次吗?其实是我拿的,我妈审问了我一天,我硬是扛住没说,英雄吧?二伯母又嗔又骂:你还英雄,我看你就是个大狗熊,一点小事都不敢承认。
大家都笑了,我没笑。谁也不知道,那个你们眼里的小事如何将一个少女间接地变成刽子手。
我举起酒杯:来,为10年后终于洗脱我当年的冤屈,干杯!
一桌人面面相觑。我一仰而尽,然后独自走到酒楼的阳台。
夏日潮湿的热气扑面而来,我翻开手机,里面有一条保存了两年的短信:这辈子受伤最痛的有两次,一次,失去父亲,一次,失去你。谢谢你,曾在我最低落的时候照顾我。——杜小鸣。
那年去深圳前,我拒绝了杜小鸣的求爱。两年前,他辗转打听到我的手机号,然后,发了这条短信。我才明白,我的无知曾伤害了他两次。
在他们班的校友录里,我得知了他的现状,在南京一家化工厂上班。相册里,他笑容满面,身边依着一个温柔的、已有孕的妻。
这是整场青春记忆过后,我唯一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