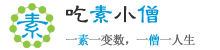对于凡俗的夫妻,说起爱情来,总是奢侈的。很多夫妻毕生未曾言爱,却一言一行间,无不蕴藉情意。
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形式大于内容的时代。因了日益膨胀的物欲蛊惑,很难有人在恋爱时能将一切撇清,均不与利益挂钩。貌合神离是大多数,搭手过日子也是勉为其难,看似美满的婚姻很多时候竟也是一种形式,情感不由灵魂做主,终日在心之所向的生活与爱情之外逡巡不前,就是没有追求新生活的勇气与力量。这样的日子已成沉疴,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惟有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
如此形势之下,人们不由得燃起对于古典、朴素情爱的渴望。毕竟此生漫漫该怎样度过,才算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岁月?自然是有情有意,温情常驻。
相对于大都市华丽的步调与旋转的速度,小地方的凡俗夫妻反而更有条件过足烟火气息浓郁的日子。或许,惟有慢步调去生活,方可将所有的滋润体味得淋漓尽致。
看惯了多少流散于各大媒体杂志的名人爱情,那种似乎千篇一律的叙述笔调已然令我们麻木,就如同吃惯了山珍海味,倒真真切实地盼望能够返身乡野,重拾野趣,重品野味——因为,我们原生态的生活与爱情,全在那里,城市只是乡村的纪念碑,而已。
她是苏北煤矿里一名普通的家属,丈夫日日穿藏青色的工作服、戴黄色的安全帽、蹬长及膝盖的黑色胶靴下井,是一名同样平凡的井下工人,过着三班倒的日子。每天迎接她的,总是丈夫略带疲惫而覆满了煤灰的一张脸,她并不觉得这是砢碜了自己,而是每每无声地端上一盆清水,轻轻沿盆搭一条毛巾后,便默默走开。是的,她是在等待丈夫,但是,还有那么多的人事在等着她,比如她的两个孩子,比如,矿里那两条梧桐掩映下的马路。
等着她的两个孩子,是她心里永远的怜惜,永远的痛。尤其是那个瘸着腿且患有痴呆症的儿子。但凡做了母亲的女人,心境总是较单身女子不同的。更何况她只是这样一个平凡朴素的女子,在这个煤矿,连个正式工都算不上,更谈不上所谓的编制,她只是一名下井工人的家属,一个来自苏北乡下的小媳妇,跟随丈夫来到煤矿里来讨生活,并相夫教子。可是,母亲这一平素的身份,在她身上却闪耀着异常夺目的光芒,一切,都只因了那个残疾的儿子。
一个平凡的母亲,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悉心照料自己残疾的孩子,不离不弃,且无怨无悔,这俨然已不是平凡,是不需被镌刻在功德碑上的伟大,是尘埃里开出的朴素动人的花。
等着她的矿里的那两条梧桐掩映下的马路,则是领导给予她的工作,她视之为自己修来的福分。作为一名职工家属,相夫教子是本分,凡常的家务已令其忙得不可开交,可是她不行,她还有两个正在成长的孩子,她不能这样轻易就跪倒在无力的生活之下,永远生活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她要用自己柔弱的双肩,为丈夫分担掉一些经济负担,分担掉一些因生活的贫困所带来的身心苦痛。
是她的善良与沉稳,为她迎来了这个光荣的扫马路的工作。从她日日甜美的笑靥与时时对路人亲切的招呼来看,她并不认为扫马路是一件丢份的事情,相反,很荣耀。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换来的血汗钱,踏踏实实,贴心贴肺,捏在手中也觉得别样的沉甸甸,作为一名普通的妇女,她就认这个理。
就这样,这有些特殊的一家四口的日子,如同其他所有煤矿职工的日子一样,随着每个日升日落的晨晨昏昏,安稳密固地过了下去,淙淙一如小溪的流淌。
有人试着问她,如此辛劳的日子觉得苦吗。她腼腆地笑笑,下意识地用手将一侧的碎发掳至耳后,缓缓地说,就这样,挺好的。
挺好的。这个平凡的女子是这样的易于满足。或许终其一生,她都没有机会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什么是华丽,什么是潮流——不,她不需要谙得那些所谓的时尚,包括衣物,包括生活,甚至包括爱情,仅仅就是这样安分地守着三班倒的下井的丈夫,守着两个正在成长的孩子,守着自己那份来之不易的每月500元的扫马路的工作,她已经十分满足,她的脸上每天都洋溢着欣慰的笑,就像一朵开在春天里的不知名的花。
那么,作为一个女人,难道她对爱情没有憧憬吗?作为局外人,我们只能隔岸观火,这样的问题,是怯于硬生生向她提问的。因为在爱情之下,就连我们这些外表光鲜的人,都会一霎时化作一个个委顿的影子。可是,从她有条不紊地操持家务的平静里,从她丈夫虽疲惫却温情的笑容里,从女儿健康活泼的成长里,从儿子日日的宁静神态里,我们已经了然——爱情对她,远不只是一个名词,或许今生她甚至没听说过爱情这个浪漫的名词,可是她平时温情的一举一动,她悉心张罗的一粥一饭,她随意漫开的一颦一笑,无不在淋漓尽致地阐释着爱情二字。
丈夫与孩子们的安稳,就是她的爱情;每天起床后还能扫马路,就是她的爱情;日日沐浴在和暖的阳光下,偶尔与路人亲切地打一声真心实意的招呼,就是她的爱情——整个的生活,漫长的岁月,都是她的爱情。
至此,是否我们一时间皆已相形见绌了呢?华丽奢靡的时代背后,我们更需要握一丝清醒,攫一丝力量,如同一株懂得叶落归根的大树一般,时常反思自己,反思平凡之中的伟力,反思我们到底应该以怎样的一种姿态,无怨无悔地接受、并拥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