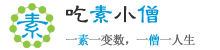父亲宽阔而又有些佝偻的后背,是我童年里最为刻骨的记忆。
学校离家甚远,但有公车。可小学六年,我都没有坐过一次公车。父亲坚持要用他那辆笨重的凤凰牌自行车接我,一接便是多年。
每次放学冲出校门口,我都会以最快的速度收敛起自己的劣态,恭恭敬敬地走到父亲跟前,等他把我抱上后座。很多时候,他会心疼地问,跑那么快做什么啊?爸爸会一直等着你的。下次慢点儿,知道吗?我用力点点头,催促他快些回家。他似乎不知道,我之所以跑那么快,并非怕他久等。而是因为怕同学们看到,我有那么一位贫穷而又不懂着装的父亲。
回家的路上,有一家贴满糖纸的福利社。每每经过那个福利社门口时,父亲总会下意识地停下,他知道,我爱吃里面的一种名叫变色龙的糖果。我安稳地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等他归来,朝我大张的嘴巴里丢进一枚或青或绿的糖果。而后,他呼哧呼哧地蹬着自行车,在田野间的小路上。我用力吮吸着酸甜的糖果,将染了颜色的舌头努力地伸出来给他看,他哈哈地笑着,这是我童年印象最深的一幕。
后来,我念高中,再不喜欢他来接我了。可我不敢说,我知道父亲向来倔强的性格。于是,每每我总是第一个奔出校门。偶然,与父亲闲谈的家长们会说,你女儿真懂事,怕你久等,一下课就跑了出来。父亲总是笑笑,不语,双手死死地撑住自行车,等我上去坐稳,他才缓缓地蹬起踏板,在宽阔的马路上迎风而行。
父亲再不会抱我了。我长大了,有了少女的矜持,和一些难以名状的隔膜。当然,我也再不会央求父亲给我买那些花花绿绿的糖果。我告别了童年,告别了羊角辫的时光,也告别了酸甜的、可将我舌头变色的糖果。
偶然,我在家漫不经心地对父亲说,爸,以后你就别来接我了吧,学校离家那么远,反正有公车。父亲抬头瞅瞅我,低头接着咣咣地敲打着木头。我以为,他不会再来接我了,可当我第一次放弃奔跑,心无顾虑地、悠然地走出校门时,才发现他已在门口久候多时。
我阴沉着脸,歪坐在他的身后,只字不语。他似乎觉察到了我的不悦,一路上故意将车速放得很慢。他当然不清楚,自己的女儿为何在那个年纪悲喜不定。
其实,我喜欢上了隔壁班的一个男孩。只要父亲不来接我,我就可以坐上公车,和他走上那长长的路,相伴那短短的时光。可父亲从始至终都没有做出让步,我想,他应该是知道的,所以,故意用这种无声的方式来阻挡我初恋的懵懂情怀。
高三那年,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住校,我说,学习太过紧张,我得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学习。父亲破天荒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可周末回家的时候,他仍旧坚持来接我。
那时候,我已经和那个有着剑眉的男孩交往了。每晚自习后,他都会将我送到宿舍门口,而后,一步三回头地消失在幽深的校园小径深处。我开始走神,开始失眠,开始有了无数个莫名其妙的念头。后来,他在课上给我写情书被老师发现了。我以为,他会一五一十地将所有的罪状都坦白。殊不知,他却一人承担了所有的后果。他说,那是第一次给我写信。
他的父母执意要他转学。他临走那天,我们都不曾见上一面。就这样,那场纯如梨花白如雪的初恋惨淡夭折了。
那个阴雨濛濛的下午,我在父亲的背后一面努力地撑着伞,一面哭得不能自已。后来,他兴许是发现了,竟然停下身来,与我一起,悠然地在田间小路上散步。我记得那条路上,他曾喃喃地说,人生总是要去经历一些事的。
之后,天平已经失衡的我,只能将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了高考这一边。考场内,无论怎样地忐忑不安、惊心动魄,只要出门看到父亲,我的心会瞬间平定。
后来,我北上念大学,一年一回。每次归家前,父亲总会将我乘车的路线和到站的时间盘问得清清楚楚。而后,用那辆已是破旧不堪的自行车,载我回家。
大学毕业后,我放弃了留校的机会,毅然回家,在城里找了工作。没过多久,我按揭买了辆车。心想,这样,父亲便不用来接我了。
我打电话跟父亲说,爸,我这个周末想回家,和一个朋友,你和妈在家等我。他在那头说要来接我,我说,不用了,我买车了。
等我开车经过那个福利社门口时,恍然见到在炎炎烈日下,靠着自行车一动不动的父亲。我下车,拉住他的手说,爸,不是叫你不要来接我了吗?你看,都等多长时间了?他拍拍我的肩膀道,回家再说。
燥热的田间小路上,我多次停下,拉扯着父亲上车,他执意不肯,说上了车后,自行车怎么办,再者,没换衣服。我了解他。于是,只能与朋友无奈地坐在冷气徐徐的车内,跟着后背佝偻、大汗淋漓的父亲,慢慢前行。
一路上,父亲无数次回头看我。朋友终于忍不住问,你爸怎么老回头看我们呢?这样可不太安全。
我忍住热泪,平静地说,他一定是怕我忘了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