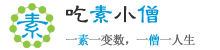那对父子,是我在火车上遇见的。他们是从武昌站上来的,一老一少,每个人背上手上都拎着大小不等的包。父亲大约五十多岁,个儿不高,被整日的风尘打得黝黑。儿子的模样像极父亲,只是带着那个年纪特有的一种张扬。上了车,父亲忙着往行李架上放包,儿子已经利利落落地爬上了铺位,耳朵里塞上耳塞,车厢里的世界便与他无关了。
应该是父子两个只买了一张卧铺票。父亲没有铺位,就坐在窗口的小座位上,看着儿子说:到了学校,要跟同学搞好团结,没有钱了就给我们打电话。我笑着接过了那位父亲的话,问:是去送孩子读书的么?是的,考了南宁大学,我和他妈一辈子吃尽没文化的苦,到他,说什么也要把他送出去。父亲的眼睛一下子就亮起来,挺了挺上身,满脸都是骄傲。他太需要一个人,来同他一起分享那份喜悦了。
车到长沙,已是晚饭时分,餐车服务员推着小车走近我们。父亲起身递给服务员一张十元的票子,要了一个盒饭,递到了儿子手上。他自己则从包里找出一张黄黄的饼来吃:我最吃不习惯火车上的饭,这是他妈给我做的,要不,给您点儿尝尝?看他用一双粗糙的大手一点点撕着有些发硬的饼,另一边的儿子却拿着一个盒饭不紧不慢地吃,连让他一下都没有,我的心,忽然紧紧地疼了。也许,因为儿子还太年轻,还不懂得如何来体恤自己的父亲。那年那月,我不是也曾如他一样,被父亲一路护送着走向人生中的一个崭新旅程么?
1994年9月,我去北京读书,那是我和父亲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到了晚饭时分,我和父亲还在火车站前广场的水泥地上坐着。父亲怕我饿,就掏出包里的点心给我。不知道那张包装纸是什么时候被风卷走的,只等我们站起身要抬步时,一位戴着红袖章的中年男人大步流星地走过来:罚款五块!我一时反应不过来。
父亲的脸却立马被一层讨好的笑给笼住了:同志,请高抬贵手,我们没注意到纸被风吹到一边了,我去拾回来,别罚吧?十块!你看,同志,这??十五!交不交?
看着对方盛气凌人的样子,再看父亲一脸奉承,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从来没有哪一刻,觉得如此难堪过:爸,把钱给他,我们走!父亲却还在同对方磨:好吧,我们交就是,就按最初的五块吧?父亲在交钱,我气咻咻地拉着行李甩开他走。
我不明白,在家里一向脾气火暴的父亲,那一刻,却为何没骨气到那种程度。他竟然一直在笑,还气喘吁吁地追在我后面:孩子,五块钱,在外就够你吃一顿饱饭,就能给你买五瓶矿泉水,咱不能跟钱斗气啊。就为了女儿的那一顿饭那五瓶矿泉水,父亲宁愿把自己的骄傲让对方践踏得无处逃遁。只是,那时,我太年轻,还不能懂。
及至我也做了母亲,才明白,为了孩子,做父母的是可以忍受怎样的煎熬。记得那个寒冬的深夜,三岁的女儿牙疼,嘤嘤地哭着不能入睡。丈夫毫不犹豫地将女儿包裹严实,没有车,就一路抱着她向着远在几十里外的医院奔去。女儿在爸爸的背上睡着了,不再哭着叫疼。那个深冬的长夜,我和丈夫就在医院的走道上依偎着,等到第二天早上牙科医生去上班。事后,丈夫一脸认真地说:我也知道去了也找不到牙医,只想着抱着孩子往医院走,对她,在心理上就是一种安慰。她不是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不知道,长大以后的女儿,再听自己小时的这段经历,会作何感想。倒是我,每次想起来,心里都有一种暖暖湿湿的感觉。
诚如那位火车上的年轻学子,也许现在还不能完全读懂父亲。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懂。懂得了的他,便会在与每一位父亲相遇时,都会如今天的我一样,愿意从心底里去心疼天下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