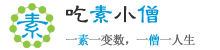初春,傍晚。重庆万豪酒店大厅外,料峭春雨淅淅沥沥。送走出席报社感动重庆十大市民颁奖典礼的众嘉宾,我陪客人来到酒店自助餐厅。餐厅富丽堂皇的装饰在灯光下呈暗红色,峨冠博带的大厨背着手,气宇轩昂地穿梭于餐桌间,神情活像巴顿将军正视察他的第三坦克军团。
客人是来自东北的一对农民夫妻,他们是来出席儿子的颁奖典礼的。
典礼结束时,头儿对我说:你陪他们下去吃个便饭吧,人家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这对夫妻年过五旬,朝鲜族人。他们当天从遥远的东北飞过来,男人戴一顶时髦的白色棒球帽,与陈旧的衣服很不协调,女人衣着款式起码是10年前的。他们的儿子叫李恒太,21岁,在重庆读大二。去年国庆节,李恒太在九龙坡长江边为救一名落水儿童被江水冲走,至今下落不明。
老两口都不高,黑瘦,与我想像的东北大汉有差距。但一开口,觉得口音很熟,让人想起赵本山,他们坐在餐桌边沉默着。男人掏出香烟狠狠吸,女人满脸悲伤,眼睛一直含着泪花。
我说,这里是自助餐,我给你们取去。男人把烟掐灭,说:我们自己来吧。我带着男人和女人穿行在香气四溢的食盘间。他们怯怯地取菜,可能不太习惯用不锈钢菜夹,女人不小心将菜屑掉落在餐台上。大厨见了,不说,也不笑,脸冷冷的。
男人和女人盛了盖不住盘底的一点素菜,坐下轻轻吃。我叫小姐拿来筷子,换过他们手中的刀叉。男人的脸稍稍松懈了一些,女人仍苦着脸。我知道他们还沉浸在丧子之痛中。
我问男人:喝点啤酒吧?男人摇头。我便去取食物,回来后,见他们已将素菜吃光了,盘子干干净净无一点残渣。我说:再去给你们取点肉食。男人一把抓住我说:谢谢了,我们吃好了。女人也将脸拾起来,眼睛定定地看着我,说:张记者,我们吃好了,真的。
我注意到,他们可能怕影响我的胃口,没说吃不下,也没说吃饱了,只说吃好了。
餐厅很安静。远处有三三两两的老外正在用餐,交谈声音如耳语。背景音乐是加斯·荷伯为电影Wemer Herzog的配曲,记得电影开篇是一个少年在金黄麦田里奔跑,它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据说,这段音乐的主题是人人为自己,上帝反众人。我想起李恒太:春天,东北大平原上,他也曾在麦田里奔跑过,如今却再也回不到故乡——他为了别人永远沉没在重庆长江段,连遗体也没找到。
请李恒太的父母来重庆前,我与他们通过电话。
我说:按报社规定,你们来重庆,报社可以报销一个人的火车票。男人说:现在春运还没结束呢,火车票不好买,我们准备乘飞机过来。
我说:飞机票呀,有点
男人听出我的迟疑,说:你们报不报销没关系,哪怕自费,我们也要来出席恒太的颁奖典礼。又说:抚顺这几天零下十几度,冷得跟咱心一样,今年除夕夜,我知道儿子回不来了,但还是给他摆了筷子和酒杯。每次一想起他,我头发就一缕一缕掉,现在快掉光了!
难怪男人戴着棒球帽。
面对丧子之痛的男人和女人,我想找点别的话。问女人:你退休了吧?女人一怔,说:我是农民。她似乎看懂了我的意思,说:张记者,你能来陪咱坐坐,我们已经很感激了,你千万不要怪我话少啊。又说:昨夜,我又梦见了我家恒太,好多鱼正围着他咬哩!说罢,她泣不成声。
男人接过话说:我们虽穷,但还是准备了1万元,如果重庆有人能找到恒太的尸骨,我们一定要重谢他!他边说边掏出钱包,取出一张合影:前面站着一个风华正茂的英俊青年,后边是满头浓发憨笑着的父亲。那父亲与眼前这男人完全成了两个人。
男人突然问:今天的颁奖会场可能要花点钱吧?我说租的,6000元。男人一呆,女人收住哭。又问:这晚餐呢?我犹豫着,说147元。是我们全部吗?男人问。我说一个人147元。哪怕只吃了一片面包,也这价。男人和女人久久无语,低下头去。
最后我问:你们明天怎么安排,需要什么帮助?男人说:不再麻烦你们了。我们准备到恒太下水的地方去看看,再给他烧炷香,也许今后也来不了了。
我无语。我想起颁奖会上,由我给他儿子撰写的颁奖词。
然而,我真的理解他们的儿子吗?汗颜。
当我把男人和女人送到酒店门外,灯红酒绿与鼎沸人声迎面扑来。接他们的车来了,女人突然弯下腰,从一个大塑料袋里掏出一个小包,说:张记者,我要送你点东西。我赶紧推辞,说我们有纪律,不能收的。女人抓住我的手说:我不听这些,你一定得收下,这是我自己上山拾的榛子,不值钱,是心意。男人说:收下吧,收下吧,感谢你给我们恒太写的那些话呢,他如果水下有知,也会笑的。跨进车门前,男人突然回身握住我的手问:啥时能来东北?我一定用朝鲜族礼仪接待你。
一周后的大清早,他们给我打来电话,说已经回到老家了。女人说:我们是坐船走的,一路想看看恒太安睡的长江。男人接过电话说:恒太妈从重庆朝天门上船后,几乎没离开船舷,一直到三峡大坝才回舱,我们知道找不到,但心不甘啊!
我久久无语。男人叫李明德,女人叫崔成莲,家住辽宁省抚顺市章党朝鲜族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