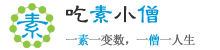回来了?嗯。
吃饭了没?吃了。
再吃一点?不用。
进门、低着头换拖鞋、我妈围着围裙从厨房探身出来问,我面无表情应两声,回卧室,关门——没关死,特留出一道缝给我在街边捡到的一个小弃猫出入用,省得它出不去进不来,蹲在门边鬼叫鬼叫。有一次我听见我妈跟我爸讲,说我待这只死猫比跟她都亲。
你活该。我在心里哼哼。
抱着笔记本上网,又听见她跟我爸说,老大房子要翻修,咱给他凑几千元钱吧。
克制不住,狠狠一巴掌拍在键盘上。
从小就这样,一直都这样,是不是等你们死了,才不这样。
吃我的饭,住我的房,给儿子装新房翻盖旧房。我是个女儿怎么了?就不是你家人了?
这老太太忒可恨!
我哥这人吧,不知道是小儿麻痹还是什么的,有点儿跛脚;小时候发高烧,脑子还烧得有点儿坏了。高高壮壮的一个人,小时候玩儿,永远扮演的是强盗、奴才、马那类角色,驮着一个挥着木剑的小人冲冲杀杀,小人儿还喊着驾!驾!当然,这个小人通常都是我。但这也改不了我对他的仇视。因为他穿着新的黑条绒千层底棉鞋,我就只有拾他的开花破棉鞋来穿,脚趾头顶被我娘用一块深蓝布堵上,真难看。我说他一瘸子,穿什么不是穿,凭什么老给他穿新的呀!我妈劈头就给我一巴掌:别人看不起你哥,你也看不起!我哥就笨笨地用巨灵神样的手掌摩挲我的头,我一巴掌拍开。
我的功课一直不错,不像他。等我考上初中,我妈实在看他不是读书的材料,才万分遗憾地罢手,送他去学木匠。学手艺比上学不少花钱,逢年过节都要给师傅孝敬节礼,平时也要三五不时请师傅来家吃饭。买一只卤鸡儿,一包羊肝,熬一锅白菜,俺们家过年也吃不上这样的好饭。结果师傅吃完后,有一点儿剩头剩脑,不等我伸手,我妈一个转身就把盘子端走,留着给我哥吃,说他干活辛苦。我心里发恨:你给我记着!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吃过一口。
我比我哥小着好几岁,但比他还早结婚。谁让我在家里得不到温暖呢。谁让我哥又瘸又傻娶不到老婆呢。
我结婚的时候,我妈给我置了两床花洋布棉被,一个红花小褥,两床花洋布褥。我想要两张绒面儿的,我妈说:咱家没钱啊。你不上着班吗?以后自己买。这一堆东西,总共没花了二百元钱,我就把自己嫁了。
两年后我哥结婚,娶了邻村一个三十多岁的大龄女青年。那叫一个丑,猪八戒都比她面善。打遍街骂遍巷,脾气差到了极点。人家要彩礼三千元。我妈眼都不眨就给了人家。还置办了电视机、录音机、缝纫机
我嫁出去后,我妈倒也时不时地蒸两屉包子送过来。然后在我的新家里摸摸看看:嗯,这电视不错,嗯,这洗衣机什么牌的?嗯,还有这录音机,比咱家的好看。我冷冷地讲:好不好看都是婆家置的,你操这心干啥。
她好像有点讪讪的,转而又强词夺理:谁不是婆家置呀?
我说:那也得娘家有陪送呀。
那不陪了你辆飞鸽自行车吗?
你把它骑回去吧,我不稀罕。
她气得没了话,坐那儿掉眼泪,数落把我养大多不容易,翅膀一硬就忘了娘。
我心烦:我就是不孝顺,你不爱来别来。
这样的风波说不清楚有多少遍。后来她就真不怎么来了。
等我买房进城,她也不来。我也不请她。
这次来,居然是为了要给我那傻哥凑钱修房,当天晚上她就跟我伸手要钱。你当我摇钱树啊,踹两脚就往下掉银子?我没钱。撂下硬梆梆一句话,我回房了。
老爸到我房里来坐,说:那个,你甭怪你妈,她
某某某你给我出来!我妈一声狮子吼神功,就把他的半截话吓回去了,起身乖乖出门。我以手覆额,这什么老婆呀。
然后就听到她在外边发飚:她待那只死猫都比待她哥亲,你还去跟她讲个屁讲!小时候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这么大,供你读书挣钱,到现在你这点忙都不帮!
我再也忍耐不住,冲出去喊:是,你是把我拉扯这么大。穿衣吃饭哪一样不是我哥占先?要不是他考不上学,你会有钱供我上?我帮忙?我自己买房还按揭贷款,你怎么不说帮我一点忙?鞋在这儿门在那儿,看不上我,打行李走人!
三年过去了。我爸脑血栓病重,我才又第一次登娘家的门边儿。自从她上次一气回家,我真就没打过一次电话,没回去看望过一次。我发现我跟这老太太挺像的,都死硬死能扛。
等你老了,我气恨恨地想,傻哥哥管不了你,儿媳妇不肯管你,我再把你接来,好吃!好喝!好穿戴!好照应!叫你看看,到底是养儿子强,还是养姑娘强!
那天,我亲眼见老爸吃力地拉着我妈的手,咿咿唔唔讲:咱村里卖地分款,能分个万儿八千的。留一半给姑娘吧。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我的泪一下就下来了。不图这俩钱儿,俺爸疼我啊。
我哥的脸上依旧开得跟朵傻花似的。
嫂子的脸黑得像炭。
结果我妈说: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出家没家,她婆家会照应她,她还要这钱干什么?留着给老大,他的孩子大了要娶媳妇的。
啊啊啊啊!
我要疯了。
这什么妈啊这什么妈啊。
果真。卖地的一万八千元钱,老太婆只给我的女儿象征性的一千元钱红包。她自己留了两千,剩下一万五,全给了我哥。这下连老公都问我:你是不是你妈捡的啊?我安慰他:不是,不是。反正以后她也不用咱养,就当没这么个妈呗。
那你爸你养不养?
养。就冲他手心手背这句话,就比我妈强!
可惜事情和我的愿望是反着来的。
我想养我爸,我爸一年后就去世了。
我不想养我妈,可是她被儿媳妇赶到我这儿来了。老胳膊老腿的,我能把她扫地出门吗?
于是电脑倒霉,一年换了仨键盘,全都中了我的铁砂掌。
不过她现在好像脾气也变了,温软了,会说好听话了,更要紧的是,会看我眼色行事了。有时候,比如说吧,在餐桌上,她一屁股坐在我常坐的位置上——那个位置其实不好,长方形餐桌,我在顶头,够菜够不着。但是我习惯了。她一坐我就一皱眉,然后她瞅我一眼,迟疑一下就起来了。再比如说吧,一棵白菜分两半,她会把菜心炒成我爱吃的醋溜白菜,菜根会剁巴剁巴包成白菜粉条鸡蛋馅的素饺子。我吃,她在一边看,看得我毛乍乍的,直发烦。
女儿吃醋说:姥姥,你光做我妈爱吃的,不做我爱吃的我妈就说:谁说的,我也做你爱吃的呀。然后拉过女儿的小手,一下一下来回翻,嘴里还唱:手心,咳咳,手背,都是肉——
啪!我把筷子一放,回房。
这下子可能把她的脾气也激起来了,好久没见她这样怒毛直楞的模样了,冲进我的房间,气势万千:喂,我们谈谈。
有什么好谈的。
咳咳。就一句话:我死了,咳咳,你得对你哥好。你要记着!咳——咳!
我我又气得说不出话来了,好好好,你死了,我把他当神仙供起来。
我妈满意地点点头,转身要走,手在门把手上了,转过头深深看我一眼,那一刻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鬼使神差转回头,正好和她四目相对,她已经把门打开了,又说,其实你哥咳咳咳咳咳!一口鲜血喷出来,我吓得大叫:妈——老公!快来!
我不知道她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多长时间,反正一发现就是肺癌晚期。一个半月后,病床上,她说话都困难了,死拉着我的手不放,看我半天。我说:你放心,不就是让我照顾我哥么?他老婆不管他,我管;他儿子不养他,我养。
点点头,她哑着嗓子嘶嘶地说,姑娘,妈对不起你。
我的泪下来了,我说这时候咱能不能不说这个。
她的嘴角扯了一个笑,攥我的手一用劲,头一歪,走了。走都要把后事安排完,真强悍。
估计我的强悍也得自她的遗传,反正后来我真的践诺了。傻哥家里的日子过得跟破布似的,我给侄子找个工作,一家伙把他踢到广州挣钱去了;又把哥哥三五不时地接过来,省得没吃没喝,挨冻受饿。
有一次,在城里偶遇一个娘家的老哥哥。他说哎哟,你跟我那小婶子(我妈)一样,都是好人!野地里捡来个野孩子,老的养了,小的接着养
原来这样啊。
我的傻娘。你咋不早说。你是不是害怕我因为他不是一脉生我就欺负他?你信不过我,还信不过你自己的心肠?你看我路上一个弃猫都肯捡回来,那都是跟你学的,不亲他,不养他,不管他,怎么会呢?
气死我了。妈,我恨你。
妈,对不起呀。